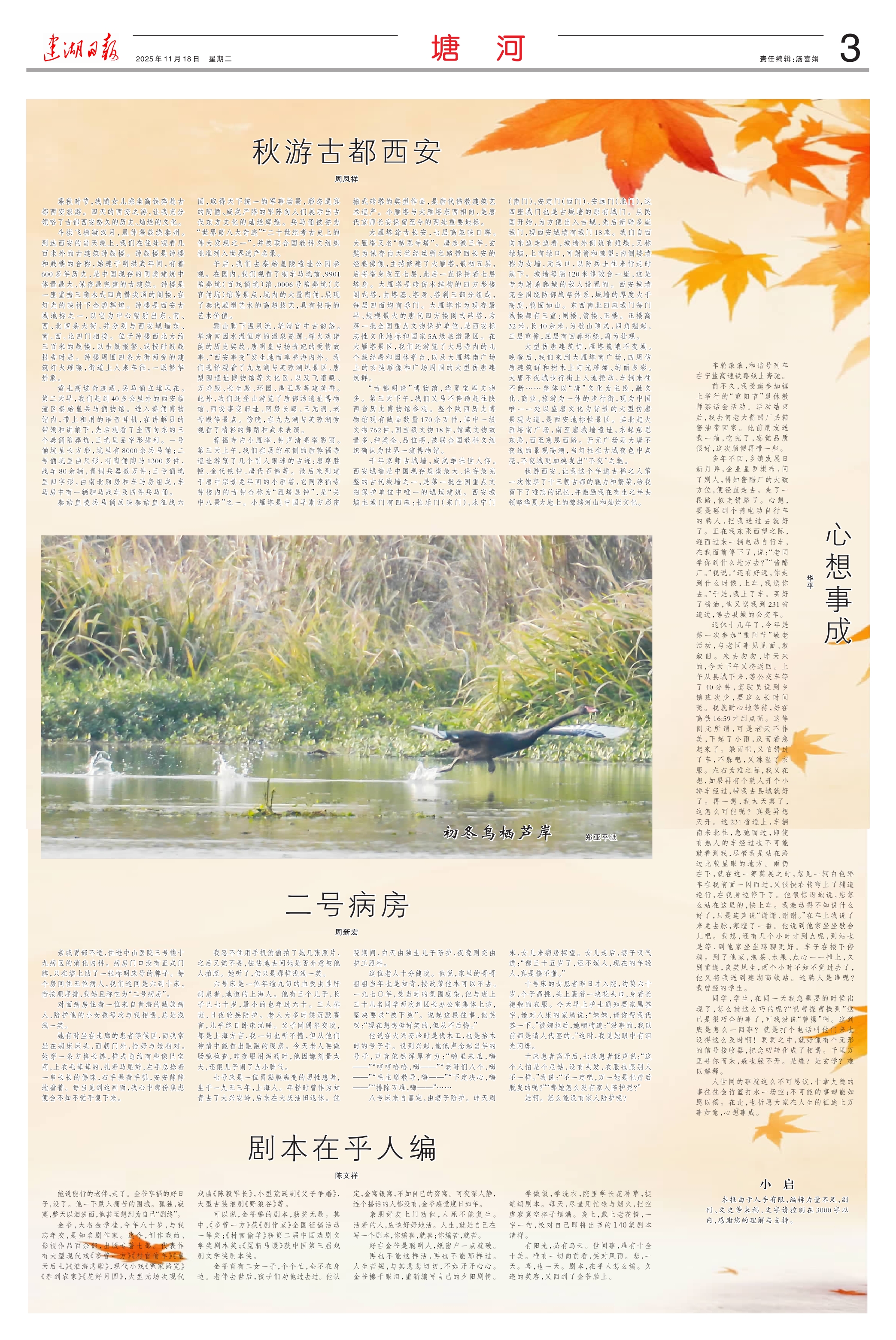内容详情
二号病房
周新宏
亲戚胃部不适,住进中山医院三号楼十九病区的消化内科。病房门口没有正式门牌,只在墙上贴了一张标明床号的牌子。每个房间住五位病人,我们这间是六到十床,若按顺序排,我姑且称它为“二号病房”。
对面病房住着一位来自青海的藏族病人,陪护他的小女孩每次与我相遇,总是浅浅一笑。
她有时坐在走廊的患者等候区,而我常坐在病床床头,面朝门外,恰好与她相对。她穿一条方格长裤,样式隐约有些像巴宝莉,上衣毛茸茸的,扎着马尾辫,左手总捻着一串长长的佛珠,右手握着手机,安安静静地看着。每当见到这画面,我心中那份焦虑便会不知不觉平复下来。
我忍不住用手机偷偷拍了她几张照片,之后又觉不妥,怯怯地去问她是否介意被他人拍照。她听了,仍只是那样浅浅一笑。
六号床是一位年逾九旬的血吸虫性肝病患者,地道的上海人。他有三个儿子,长子已七十岁,最小的也年过六十。三人排班,日夜轮换陪护。老人大多时候沉默寡言,几乎终日卧床沉睡。父子间偶尔交谈,都是上海方言,我一句也听不懂,但从他们神情中能看出融融的暖意。今天老人要做肠镜检查,昨夜服用泻药时,他因嫌剂量太大,还跟儿子闹了点小脾气。
七号床是一位胃黏膜病变的男性患者,生于一九五三年,上海人。年轻时曾作为知青去了大兴安岭,后来在大庆油田退休。住院期间,白天由独生儿子陪护,夜晚则交由护工照料。
这位老人十分健谈。他说,家里的哥哥姐姐当年也是知青,按政策他本可以不去。一九七〇年,受当时的氛围感染,他与班上三十几名同学两次到区长办公室集体上访,坚决要求“被下放”。说起这段往事,他笑叹:“现在想想挺好笑的,但从不后悔。”
他说在大兴安岭时是伐木工,也是抬木时的号子手。说到兴起,他低声念起当年的号子,声音依然浑厚有力:“哟里来瓜,嗨——”“哼哼哈哈,嗨——”“老哥们八个,嗨——”“毛主席教导,嗨——”“下定决心,嗨——”“排除万难,嗨——”……
八号床来自嘉定,由妻子陪护。昨天周末,女儿来病房探望。女儿走后,妻子叹气道:“都三十五岁了,还不嫁人,现在的年轻人,真是搞不懂。”
十号床的女患者昨日才入院,约莫六十岁,个子高挑,头上裹着一块花头巾,身着长袍般的衣服。今天早上护士通知要家属签字,她对八床的家属说:“妹妹,请你帮我代签一下。”被婉拒后,她喃喃道:“没事的,我以前都是请人代签的。”这时,我见她眼中有泪光闪烁。
十床患者离开后,七床患者低声说:“这个人怕是个尼姑,没有头发,衣服也跟别人不一样。”我说:“不一定吧,万一她是化疗后脱发的呢?”“那她怎么没有家人陪护呢?”
是啊。怎么能没有家人陪护呢?